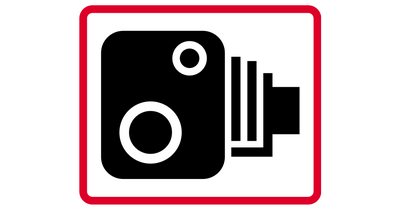HCB(九):觀世之道

不參與、不干預,這就是布列松看世界的方法。
布列松討厭賣弄技巧,在攝影上尤其如此,他認為生命本身已經夠有趣了,不必再故做驚人之舉。他贊成任其自然,而決定性的瞬間,與其說是一種技術,不如說是一種「觀世之道」。
那麼,這種觀世之道又是如何呢?我們可以發現,布列松本人也是採取現象學式的觀察,那就是“As the thing the way it is”,還原事物本身應有的樣貌。用事物本來的面貌,去訴說事物本身,所以,大家的評論才會是「真實」兩字。
已在前文提過,比起何時按下快門,按下快門前的思考與觀察,才是重要的。在「決定性瞬間」發揮作用之前,必須要有完整而詳盡的觀察,如此才能拍出讓當地人感覺「真實」的照片。這說起來很容易,只需觀察即可,但一名外來者在短時間內能拍出讓當地人感受到真實的相片,這又有多難?
若有攝影基礎的讀者諸君,不妨試試便知。但思考與觀察,又干「決定性的瞬間」何事呢?這是在書寫過程中,最常被問到的問題之一。這乍看之下是沒有關係的,但只有對「決定性的瞬間」存而不察者,才會問這類問題。
我們重新審視「決定性的瞬間」這個語彙。瞬間,自然是指按下快門的那一刻,可以說是技術上的選擇。但「決定性」這個詞,就是一種哲學上的思考。這怎麼說呢?因為若不是對事件整體的來龍去脈與因果關係做通盤式的瞭解,不對現場狀況做個完整而透徹的觀察,你又如何能得知哪個時刻才是「決定性」的時刻呢?
另外來看,非決定性的瞬間,就是拍攝人為的佈局,或是導演現場,這就不是「決定性的瞬間」。因為它不自然。捕捉自然發生的鏡頭,是布列松另一個堅持的想法。他反導演現場與反賣弄攝影技術,這是應與他攝影哲學並置的,因為他是攝影記者,使命就是冷靜地由外部觀察這個世界,所以他曾說過:「對於事件,你永遠是局外人」。不參與、不干預,這就是布列松看世界的方法。也就因此,他才能捕捉到自然,對他來說,能捕捉到自然的存在,那就夠了。
這裡我們知道,對他來說,「決定性的瞬間」,其實是一種存在,一種在自然界中巨大的存在。只有心思細密的觀察家,才可以發現與捕捉這一刻。但人為的佈局與導演,早已偏離了自然的軌道,所以,不管構圖再怎麼精良,控光再怎麼準確,那都不是「決定性的瞬間」。
所以他說:「相機只是一種素描世界的工具。」身為一位攝影記者,他做的是深刻瞭解事件脈絡,精準掌握現場狀況,經由這種思緒與觀察,布列松才能判斷何者是、何者不是「決定性的瞬間」。

1973.05.09,Henri Cartier-Bresson,蘇維埃廣場。
〈HCB(三):布列松其人〉中曾提到,布列松是第一位進入共產俄國的西方攝影記者,儘管本文所選的相片並非他初次入俄時所攝之相片,但卻是他退休前最後一次境外新聞攝影,這也象徵著我們的連載即將在下回結束。
布列松在東西冷戰時期能進入「鐵幕」,在「新中國」鎖國時期能進入紅色大地,不只是因為他的名氣、實力,更兼有布列松的親共立場。
受中國國民黨殖民教育長大的朋友第一反應應該是:「怎麼可能?!」
但事實上就是如此。
若非布列松的左傾立場[1],他也無法在「新中國」建立後繼續進出中國。
那麼,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沒想過,你會因為這種事而驚訝,就代表你不瞭解這位作者,如果不瞭解,有可能瞭解他所提出的概念嗎?還是你瞭解的「理論」只是二三流的轉述、只是不學無術的網站編輯胡言亂語、只是滿手鏡皇滿嘴修圖的攝影大大夢囈,或是自己望文生義的解釋?
回頭看看布列松,他出生於法國相當富裕的資產階級家庭,但他自幼就不願與父親一起行商,對於天主教也不甚滿意。
雖然他從未加入共產黨,但他的思想與當時左傾的知識份子是一致的。
20世紀的30年代,面對當時撲天蓋地瀰漫歐洲的法西斯威脅,年輕的布列松說:「希特勒並非與我們無關!」並加入了當時的革命作家組織,此時他協助了尚雷諾拍攝《生活是我們的》,而這部片只有尚雷諾與布列松是以「協助者」身份拍攝,其他的主要工作人員、演員都是共產黨員。
西班牙內戰爆發後,德國納粹主義與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合謀的態勢益發明顯,對此危機布列松並未置身事外。1937年,布列松以導演身份開拍了《生命的勝利》[2],布列松以畫面描述了左翼共和黨對醫療、衛生與飲食所做的努力,儘管本片充滿說教意味,但布列松以高度的藝術技巧讓人有繼續觀賞的動力。
「我們都是左派,這無所羞恥,亦無可炫耀。」
他的左傾立場、反法西斯、反納粹與對法國資本主義的厭惡對欣賞者而言亦非「與我們無關」。他對既有體制與主流的反抗,不只從他的相片看出,更可從他選擇當時被認為是爛相機的「萊卡」明瞭。
自墨西哥返國後,布列松替共產主義者報紙《今夜》與雜誌《目光》發稿,直到他參戰。戰後,他在中國親眼目睹中國國民黨貪腐政權的崩潰與中國共產黨軍隊的勝利。在這過程中,國民黨治下的經濟災難[3]與國民黨軍隊逃亡的敗象都透過他的鏡頭,告訴了全世界。
各位,知道這層過去,明白為何這位被稱為近代新聞攝影之父的布列松,在台灣中文資料這麼少的原因了吧。在中國國民黨白色恐怖時期,連「馬克吐溫」這位道道地地的美國作家都被當成附匪書籍被查禁[4],像這種貨真價實根正苗紅的為匪宣傳叛亂份子當然是要(在島內)消滅的對象。
回到這張相片,這是1973.05.09在列寧格勒紀念戰勝納粹黨的慶典。一般的攝影記者,都會拍下閱兵、煙火、遊行等官方安排好的畫面,但正如〈HCB(六):攝影作為一種賦形〉中所提,布列松是不會浪費底片在那種景象上的。
但是,他為何選擇這個畫面呢?
二戰結束後,透過自己的親身觀察,布列松益發清楚這廣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並非依循馬克斯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反而更像是他們之前的敵人‧法西斯份子。
透過小女孩厭惡與反方向的視線,預告了曾經是他寄望國度的未來。
延伸閱讀:
英國新聞自由考(四):新聞自由的詩樂園
新聞傳播科系的學生都知道,不,實際上是這樣,都應該聽過《新聞自由請願書》,這本書又被譯為《出版自由請願書》、《論出版自由》或《論新聞自由》。
以時間性和重要性來說,該是中文系的《詩經》或《論語》或社會系的《自殺論》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5]這種經典。
當然,經典的意思常常是「大家都知道,但大家都沒看過的書」,不過至少那些書的書名是正確的。
可是,被新聞系奉為開山祖師,提及「新聞自由」必定上溯的原點──Areopagitica,卻完全沒討論新聞,也不爭取出版自由,
反而是要消滅對手的出版品。
只要你讀完這本書,你就知道再怎麼誤譯也不可能把這本書翻成「出版自由」、「新聞自由」一類的書。
那麼,他們為什麼會這樣翻?
連受學界認可的課本都能翻成這樣,你有沒想過,網路上看來,不知道誰翻的翻譯「決定性瞬間」,可信嗎?
[1]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不同的,不過實際面很複雜,若只以反對資本主義來說則是立場一致。
[2] 本片由國際聯合衛生會出資。
[3] 見〈HCB(七):決定性的瞬間˙前──本質〉
[4] 因為跟「馬克斯」太像了,另因此理由被查禁的還有馬克斯‧韋伯等人。
[5] 這本就是馬克斯‧韋伯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