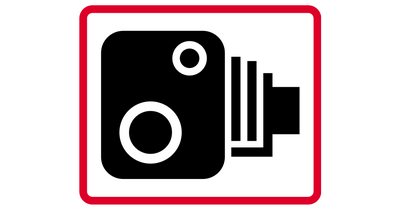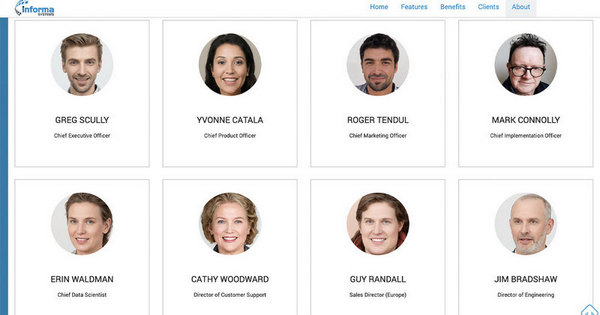[特約轉載]壹週刊攝影記者十年誌:「打黎智英工,就無諗過做到退休」
(本文附圖由編輯所加,與原作者無關)

郭仔和阿珊是師兄妹,先後入讀觀塘職業訓練中心,那是 1989 年前後的事。訓練中心的畢業生多投身新聞業當攝影記者,他們也是衝著這目標而來。入行二十多年,見證著報紙由黑白轉為彩色,圖片沒落到動新聞興起。
剛入行那年頭,新聞業百花齊放,還有早報晚報,同工勇猛「插兩支旗」早晚兼程,月入加起來可達一萬,相當豐厚。現時從業員普遍工時長,「已經無呢支歌仔唱」。兩人被解僱前正值第五次人大釋法,郭仔連續兩星期都沒放假,剛完成該期工作,就收到解僱通知。在公司打拚十年,上層不交待解僱原因,慣常的肥雞餐亦欠奉。
紙媒轉型藥石亂投 前線記者首當其衝
壹傳媒財政不穩、《壹週刊》大幅裁員已不是新聞,他們既有心理準備,卻仍有諸多不甘。媒體生態大變,紙媒急於摸索生存方向,種種混亂之下,前線工人最身受其害。「肥佬黎話要同手機連成一線,上層俾壓力,中層無方向,一片模糊,總之就要你做。」阿珊精警地說出《壹週刊》轉型的過程。
靜態照片文字承載不到影片形式的廣告,為了增加廣告收入,壹週大約在四年前開始做動新聞。剛發展動新聞時,大部分拍片工作由攝影師兼任。在現場要完成兩項任務之困難不在話下,另一個問題是,拍片跟拍照是兩樣很不同的事,懂得拍照的不一定也懂拍片,而公司提供的在職培訓幾乎是零。叢林法則在這時發揮作用,「唔鍾意咁做嗰啲會自然流失,再請返嚟嗰啲自然會做,之後就直接請 cam man。」
說起動新聞,大家第一時間想像到的可能都是蘋果日報。在網上世界,蘋果與壹週的分工很模糊。同一間公司,兩個平台做著類近的事,又似乎有著競爭關係。蘋果比壹週多一手資料,整個集團的資源也向蘋果傾斜,連剪片部也在年初搬到蘋果那邊。同一宗新聞,蘋果拍攝的短片會優先處理。壹週記者很多時都在現場遇上蘋果記者,「都唔知嗰單仲做唔做好。」但是上司總是要求人有我有,惟恐跟漏半分,記者只好疲於奔命。
阿珊想念以前的運作:「頭嗰幾年我哋唔係跑新聞咖,而係比較多做旅行、人物專訪。之後旅行cut咗,人訪改組,我地就變咗跑daily news。」從前可以花時間做訪問,用幾個小時集中影好一個人,不必像現在這樣追求速度。

編輯要求高資源缺 攝記失話語權兼貼錢返工
雖然在訓練中心主要學習拍照,但郭仔在課堂及業餘也接觸到影片製作,知識與經驗形成了一套看法,他批評道,在壹傳媒的管治下,拍片由「手工藝」變成了「輕工業」般操作。
對郭仔而言,拍攝是一件很個人的事,選材、呈現角度都充滿個人偏好。以拍照為例,即使一張照片會經過編輯、美術等程序,但拍照的內容角度、揀選照片都是由攝影師決定。拍影片的工序更多,需要有導演操控大局,此謂之手工藝。
《壹週刊》的操作是編輯主導,分工精細,拍攝、構思包裝、字幕、配音、剪片、總負責人審批,像流水作業。「cam man只係拍片傳返嚟,擺喺度。出到去用邊段,唔會知,由公司處理。」編輯連一字一句都要牢牢掌控,攝影師可以參與的部份少之又少,最壞的情況下就只是機器的操作者。
要是編輯滿足於此,雖然攝影師過不到自己那關,但大抵還不難交差。可是,編輯卻是以港台紀錄片的質素為目標。郭仔很清楚兩者的差距:「人哋有一大堆人,有收音,工程,PA,燈光,又有導演負責晒,根本無得比。」壹週上年七月大裁員過後,各組人手只剩一半,編輯的要求更難達到。而且,這要求與郭仔所理解的《壹週刊》定位相去甚遠,「不扮高深只求傳真」是壹週原本的風格,他認為動新聞的靈魂在於訊息傳遞簡單直接,並以新奇有趣的構思包裝,畫質不是第一考慮,相對簡單的器材都可以應付拍攝工作。
「想畫面有質素就應該用單鏡反光機,收聲要有幾條聲道,想要穩定影像就要滑軌……佢想你有理想作品出現但又唔俾資源你,我俾埋條命你好唔好?!」打工仔的命,高層不稀罕。立法選舉時,上司想要拍一些有塗鴉的選舉海報,著郭仔走勻香港大街小巷尋找。當時某保險推出健康程式,客戶五天內走三萬多步就可贏得咖啡一杯,郭仔走了兩天半就達標。結果上司嫌畫面不穩定,郭仔大叫無奈:「本身我已經行得多路,佢要我用單反影,單反配嘅腳架好重,點拎啊。」
去年大裁員後,這些器材大部份都要員工自費購買。一旦買了相機,腳架、鏡頭之類的其他配套就少不了。早期的相機有的只可拍照,拍片操作上不理想,例如是影片檔案過大,用作拍片的相機統統都要重新購置。除了拍攝,攝影記者還要把相片影片傳回公司,人工較高的則被要求自行承擔流動數據使費。

拍片多年從未有滿意作品 壹傳媒管理浪費人才
記者不識趣地問道,做了那麼久,大概總有些得意之作?郭仔聽到問題仰天一笑:「哈,講『得意之作』都幾奢侈」,他先是按下一肚子氣,說道:「我講個笑話俾你聽啊。」
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在九龍塘抽了三支煙之後,決定回頭,向社會揭發中共政權的惡行。討論報導構思時,上司決意用第一身的主觀鏡頭拍攝短片。郭仔解釋道,用主觀鏡頭需要大量資訊,例如是抽煙具體是在什麼時間、走哪一條路線去找何俊仁、發覺後面有人跟蹤又是怎樣的反應等等,他跟編輯反映了這個需要,對方只是敷衍了事便散水。
翌日,只有兩個攝影同事硬著頭皮拍攝。影片拍了回來,主管自然不滿意。郭仔諷刺道:「好多時唔係唔想俾啲有 quality 嘅嘢你啊,而係你掘咗個咁大嘅坑,我幫你填平已經偷笑啦。」「我同啲做影片製作的朋友食飯講返件事,笑到大家攤喺度,『乜噏嗰個唔使去跟咖咩?無 information 就去,呢啲算係做咩啫』。」
笑話說到這裡,他重新認真起來,「好老實講,我從來都無一條片睇得順眼。作為一個有良知、有認真讀過攝影、自問對電影有研究嘅人,如果覺得啲片係好,我同啲建制派嗰啲契弟有咩分別啫?」說罷他氣得啪一聲把電話摔在桌上。
「或者,呢個就係我俾人炒嘅原因啦。」郭仔嘆息道:「打黎智英工,就無諗過做到退休。」郭仔道出他視之為常識的壹傳媒經營模式:「只要覺得你江郎才盡,就會炒。之前做咗幾多嘢,公司都出咗糧俾你,無血緣關係。」郭仔形容壹傳媒是右翼,「尤其係勞工方面,依家呢種做法係合乎公司人格。」
嘴上說來是一筆清楚帳,細聽之下,又似乎不只這些。「留得低嘅,總有過人之處。應該珍惜嗰啲人,佢哋係資產唔係負累。點解今時今日仲要用最浪費嘅管理方法呢……」
他拿起還未摔壞的手機,滑著屏幕瀏覽網頁說:「依家好多資訊,樣樣免費,其實點會係免費啊。」
原文出處:「打黎智英工,就無諗過做到退休」 壹週刊攝影記者十年誌
文章經由惟工新聞特許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