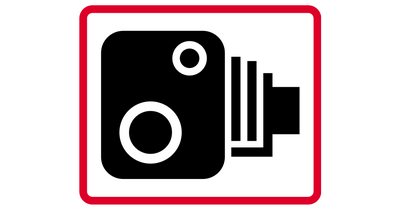岡田敦——拍攝自殘者的 《I am》

眾多自殘形式中,最常見的是界手。界手的人有兩類,一類視界手為手段,一類以界手作為宣洩途徑。要分辨兩者並不難,他們之間最明顯的分別是前者不會刻意遮蓋傷痕,甚至會向人展示;後者則會將傷疤藏得嚴嚴實實,生怕被人發現。
筆者在求學時期遇過這樣的女同學——平時不怎樣與人交往,看上去像是十分文靜的女生,但夏天仍穿著厚厚的毛衣。但有次看到她和其他女同學扭打著玩,毛衣一扯高後,手臂露出一條條血痕,嚇了一跳,仿彿窺看了他人最深沉的內心世界,未己女同學因家庭問題退學,但那白晢的手上的界痕,多年後仍令人難以釋懷。

這輯由岡田敦拍攝的作品,再次喚起筆者的記憶。在日本殿堂級的攝影大獎「木村伊兵衛賞」的眾多得獎者中,這輯算是較為異色的一輯。在這輯拍攝自殘者的 《I am》中,他找來了50位左右10-30 歲的年輕女性自願者。她們半數以上有自殘經驗。岡田將他們的臉與身體刊載在攝影集不同的頁面,讀者看的時間並不知道是身體的主人是誰、傷口的主人是誰。
在那一道又一道已經多到數不清的傷口的雙手上,縱然讀者們無法透過影像的呈現,瞭解那些傷口底下的故事,但透過最直接的視覺,讀者都可以感受到生與死的之間那種反覆掙扎累積之下、強大的壓迫感。

岡田說:「我想重現他們眼中這樣一個不同於大人看到的世界。我想拍出能直達內心深處的東西。」
在東京工藝大學的攝影棚裡,一位全裸的 20 歲女性自願者,身材纖瘦,房間裡照得通明。她緩緩的取下手腕的繃帶,透明的白色肌膚上出現無數的傷痕。「其實昨天也有割」,她說。
「那麼我們開始吧。」岡田開始按快門,接下來四小時,攝影棚裡只有快門聲和微微的流行歌曲。結束後,自願者落下大粒的淚珠:「非常謝謝你」,穿上衣服,前往車站搭長途巴士回去。

岡田幾乎不與自願者交談:「我不是心理醫生。我拍的就是她們當時最真實的狀況,跟拍風景是一樣的。」其中一位被拍的女生說「對出版的期待成為我心靈的支柱。」「割腕這件事能為人所知,能參加這個作品,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但是業界的反應是冷淡的,拍攝完畢後近一年,都沒有人願意出版,但是岡田拼了命的自我推薦,他說每當和模特兒目光交會「她們的眼睛真誠的問我,活下去的理由是什麼?那股真摯的力量壓倒了我。」終於,06 年春天,原稿來到赤赤舍社長姬野希美的手上,她說:「竟然有這麼赤裸裸的、直視人類存在的作品,讓我十分驚訝,當下就決定出版。」負責裝禎的設計師町口景則坦承「一開始我是拒絕的」,但「她們用自己的生命向社會詰問,看到這種光景,同一世代的我們豈不也該認真起來?」
至於作者是這樣說的……「我想說的不是自殘這件事,而是現在的年輕人就是活在這樣的時代裡。人的存在本身就是美好的,但若不直接面對黑暗,就不會瞭解這件事。」
對一個去意甚堅的人來說,不太會有這樣的結果。嚴重的自殘傾向背後的原因很多,但最後能看透的人往往少於一不小心就跨過死亡界線的那群。我並不知道這些女子為什麼會入鏡拍攝可能是自己最不願意示人的生命中的傷痕,但透過攝影,相較於照片觀眾們,除了無比的勇氣以外,這些女子面對鏡頭看起來更像是一種解放、一種自省。

岡田敦網站 (網站圖片極為寫實,部分為限制級。未滿十八歲看不得,
(道歉啟事: 經影思站長提醒,我們文章和其網站文字有相同之處,Photoblog除了從日文網站翻譯外, 亦有經相熟的大陸網站轉戴內容,我們查證後對方可能亦是從影思的博客直接抄寫內容,特此向影思致歉,並附上其網站之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