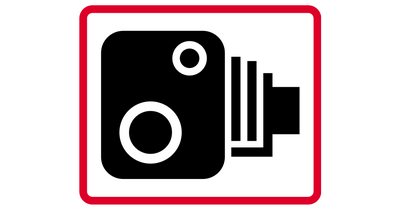影像文化與香港中產社會

(編按:來自讀好書網站的超級精彩文章。請不要被標題或文者長度嚇倒,對每位攝影愛好者來說,都值得花15分鐘細閱。受訪者是自資深攝影記者謝明莊。這篇訪問是現在無論是香港甚至是世界的影像文化最深刻、最深入的批判。從我們對攝影態度的反思,再令我們想到教育制度是否成功及社會核心價值到底在哪裡)
文:李澤文
圖:張浩賢
今天已是全民攝影的年代,拿着iPhone拍完照,立即按send便可在微博及Facebook發佈。朋友見到表示「Like」,一個圖像創作的過程便完成。
全民攝影後,專業的影像創作人究竟如何自處呢?謝明莊,專業創作人,由攝影記者走到今天成為攝影工作坊策劃者,教導影像創作技巧與概念。
香港人人拍照,但不等於人人創作,只因按下快門那一刻,背後的思考過程才最重要。而我們最欠缺的,就是這種獨立思考!
讀: 《讀書好》
謝: 謝明莊
讀:現在是否已經是全民攝影的年代。
謝: 對,所以就連攝影節都用上了「攝影為人人」的口號。
讀:數碼攝影及iPhone時代人人都想創作,人人可以創作,人人都可以立即發表自己的創作。當攝影已成為全民活動時,作為一個專業攝影師,還有甚麼意義?
謝: 我覺得先要討論甚麼是創作,在我理解中,大部分拿起相機去攝影的人,都沒有想過這件事其實是創作。
讀:為甚麼不是?我自己拍照有取景有構圖,也是創作。
謝: 在廣義層面來說,沒錯。按一個掣,也有一個影像出來,但那是否就是一個創作呢?這就是要討論的東西。
讀:看你怎樣去定義創作。
謝: 很簡單說,我們自小以來,先不要從相機來說,我給你一張紙、一支筆,你也可做到一點東西出來,那是不是一個創作?從另一層面看,如果我們當那是創作,那是否好的創作?我們如何去界定那是作品?這是我們要討論和尋求論點去支持的東西。若從一個很闊的角度來看,我真的創作了一件事出來,真的是按了一下掣,就給出一個影像來。
讀:跟着我將它發表,之後又有人讚好,又有人「Like」,這就完成了一個作品的過程。
謝: 那是一個過程,但那是否一個創作的過程,我想要細心看看。因為在討論創作的時候,那一定還有一些事情在後面。
讀:創作的定位在哪裏?
謝: 要看動機,看看個人是否真的想通過影像去分享他的感受,去表達一些意見,或者他純粹是一個記錄,還是「貪過癮」,就拿相機去拍下它。我想那是有不同的界線存在的。
剛才我講創作intention,第二要講創作水平。當我們討論創作時,是講行為本身還是講內容呢?以及你想呈現甚麼、想表達甚麼?現在大家都拿着相機,但他們不是很關心圖像本身,即拍到的內容,而是關心攝影這個行為,例如今天去某餐廳吃飯拍下每一道菜。
現在的專欄佔我寫作數量的三成,它是我參與社會的平台,其他部分的寫作是比較私密的,累積後也會出版,也會試着寫小說,可望明年出版短篇小說。其實心裏也有很多題目和念頭,文體只是一種格式,有些念頭適合用散文就用散文寫,有的適合小說就寫小說,甚至有些音樂練習可以用詩表達的也會嘗試。
讀:你覺得行為不重要?
謝: 我覺得現在所謂的全民攝影是一個攝影行為,大家都喜歡攝影這個行為,這是很trendy的事,不是很關心相片內容。
讀:他們也是關心的啊!因為他們的friend 「Like」。
謝: 就是因為friend 「Like」,好,我今晚去一家餐廳吃小籠包。OK,我喜歡!那喜歡的意義在哪裏?是在小籠包之上嗎?但得回一個「Like」,沒有實質的內容。喜歡的是構圖?是拍出來的味道?或是讓我也很想去那間餐廳吃個小籠包?
讀:大家可能是喜歡小籠包,而未必是小籠包那張照片。然後,他就會喜歡那個在網上發表小籠包相片的人。
謝: 所以我的論點就是在影像上,因為那個人放上去,他是你的朋友,或是你喜歡的人,所以他放甚麼你都會「Like」,論點是不在相的內容上,現在大部分影相的人都把重點放在行為上。
讀:所有藝術創作的技術層面都走向大眾化,包括相機,以前又菲林又黑房,又有不同的曬相技術。現在不用了,用Photoshop修一修甚麼都完滿。然後,我們會發現業餘的影響力愈來愈大。
謝: 我不清楚是不是影響大,但愈來愈多人參與就一定,我們看得愈來愈多,但也愈單一。
讀:你認為過去幾年,最轟動的攝影作品是來自業餘的還是專業的攝影記者?
謝: 最轟動的是甚麼?
讀:就是陳冠希事件和那些照片。
謝: 那很明顯不是一個藝術創作,只是那個拍攝者自娛的事情。
讀:假如今天他走出來說,這是一種藝術創作,那是一種行為藝術。幾年前,拍攝一些曾與自己發生關係的女明星,然後用一種藝術方式將它記錄下來,然後賦予它一個藝術的意義。
謝: 影像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它的interpretation,很多時候需要靠statement去切入。
讀:所以說去到最後,專業攝影和平民攝影的分別就是statement,不只是intention那麼簡單,不是拿起相機那一下。
謝: 我沒有這樣子的感覺,分別都是在intention,到底都是要看你想的是否與創作有關,到底你是想影小籠包,還是想創作?那真的是兩個不同的想法。
讀: 就是他按下相機那一刻,腦子裏在想些甚麼。
謝: 他有沒有意識,有沒有組織去做那件事。但也不能說沒組織,事實上都是有組織的,就算我們完全不去理會技巧上的東西,你也需要想想要怎樣的框架和構圖。我承認那正正是攝影行為來到這個階段,已變得模糊的原因。
城市觀察
讀:既然人人都是攝影師,學生有甚麼要跟你學?
謝: 就是討論相片的內容,你那張相究竟想表達甚麼?能不能做到你所謂的效果?香港目前教育都只注重文字教育,視覺教育很薄弱。我覺得這會是個很危險的年代,我們現在的教育制度是回應不了目前香港的現狀。
讀: 我舉個例子,剛才去蘭芳園買奶茶,拿出這張十元,其實你完全看不出這張十元想表達甚麼。我還記得當年還是記者時,金融管理局局長出來解釋這個設計,說設計這種東西見仁見智,最重要防偽,但全世界也沒有一張鈔票是這樣的。你別以為他在胡扯,其實正正反映了香港一個問題,就是他們覺得專業的設計、藝術欣賞是不重要的。你看到全世界的人都不是這樣的。在香港,視覺教育完全沒有,像你說的,要展開一張相的內容討論,都不知道從何開始。
謝: 所以我說香港是完全沒有到達後現代的地步,因為大家仍然相信權威。廣告的威力仍然很大,潮流怎麼來?今年穿甚麼流行甚麼,大家就跟着去,因為他們不懂分析圖像,不了解那些東西就跟着去,在香港是可行的,所有事情都一窩蜂,因為根本大部分人沒有獨立的圖像思考能力,見到甚麼東西就跟着那東西去做。
讀: 現在任何人都很可能擁有超過一部以上的相機,一部手機就已經是很好的相機了,為甚麼反而不是由量變出現質變?
謝: 我們可能很難在很短的時間出現改變。我們回看歷史,攝影真正開始普及講的可能是過去這三五年的時間,真的數碼化之後延伸的第二波才開始普及。不過追求的方向卻是從器材入手,而非從影像或概念入手,倒轉了是因為沒有人提供視覺教育。來到這個年代,自學攝影是最容易的一個步驟。你拍完可以馬上看到成果,不行就再拍。現在沒有以前那個問題,我要拍完三十六張之後,再去沖曬才能看到。我可以說在數碼年代自學是最快速的方法,如果你真的肯花時間去做的話,你拍完,很誠懇地問自己拍得好不好,不好,再拍,拍到好為止,馬上可以看到成果。如果那人有決心去做,其實是很容易做到,創作影像比文字和創作任何東西都快。
讀: 一件作品完成的cycle太快真的好嗎?
謝: 大部分人都會看自己的作品,我通常現在做workshop都是先做appreciation,用二十分鐘去做appreciation,我帶領他們去看一張相片。結論發現大部分人去看一張相片會用多少時間?不多於一秒,在網上看的就更加不會細心,除非是認識的朋友,想看看他在做甚麼,才會停留一下。
讀: 會不會是愈容易、愈快速完成的作品,人們對它的關注就愈少?
謝: 以前英國畫家David Hockney就說過,你用多少時間去創作的作品,別人就用多少時間去看。你用1/125秒去拍一張照片,我就用1/125秒去看。但如果以拍照來說,其實是個思考過程,最後才是按快門,按快門只是最後的事情,但現在大家對調,喜歡按快門,卻不喜歡思考,因為覺得這是件很trendy的事。像剛才說的,攝影已經變成一種很fashion的事,去任何地方都要拿相機去拍下來。

圖像快速死亡
讀: 我忽發奇想,比如按快門,要完成一件作品會不會更加需要一個更長時間的記錄,才能在創作的洪流中留下來。
謝: 第一就是內容,第二就是價值意義在哪裏?很簡單,我們現在看那批攝影節展出的香港十九世紀初的攝影作品,為甚麼那麼有價值?就是因為當時那幾個法國人、英國人跑來香港拍下來,留下來的底片很少,現在就變得很有價值了。前兩年開始,天星拆也好,皇后拆也好,全民皆影,你上網找天星碼頭可看到超過幾萬張相片,但有多少可以留下來?
讀: 在你提到的攝影展中,我看過一張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一張由孟買來的香港巴斯商人照片,即是拜火教商人,如摩地和律敦治等人。因為照片有獨特的歷史背景存在,記錄了早期香港一群商幫,印度、大英帝國與廣州的關係。但是天星碼頭是全民記錄,數碼攝影複製,就連立體影像也拍下來,可能一百年之後會有大量的天星碼頭記錄存在。但也註定這些圖像不會像巴斯商人那張相,因那張相可能就是唯一的記錄。當沒有了時間性和歷史感,圖像的價值會越來越低,或者根本沒有價值。
謝: 我覺得不能用以前那種價值來看圖像,就像你剛才所說的,有一張相可以記錄當時的情況很重要,即使技術不好,記錄都很重要。一百年後,可能大家有幾萬張香港的相片,這不代表歷史回溯的空間愈來愈闊嗎?但當你做資料搜集時,因為你現在沒有比較,以前留下的就只有一張,但當你有比較時,幾百張就有幾張會跑出來。這也就正正是網絡的問題,我們有很多資源,看你怎樣選。如果你問我從教育的角度來看,我們年青人要訓練的不是記憶力,不是訓練計算,而是訓練你如何建立思考的方法,有一個自己的角度。攝影來到這個年代,我覺得最大的分別是以前要考慮好、計劃好才去拍一張照片,不容有失。但現在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如何閱讀和編輯照片,大家可以拍幾百張相,但不會很細心地坐在電腦前回看那幾百張相片到底拍了甚麼。
讀: 相對來說,攝影對人的要求高了。以前很簡單,就是龍友心態,夠闊夠光不手震肯花時間去「捕」就可以;但現在進化到有很多軟件可用,就這樣隨手拍就可以,工具大家都有。所以現在講的已經不單是攝影教育、圖像教育那麼簡單,而是整個人文教育,培育年青人概念思考與表達的感性。
謝: 所以攝影應列入General Study,英國八十年代開始攝影已經是個General Study,中小學開始已經學攝影,他們不是去學技巧,而是學分析,學怎樣去看那樣東西。我們是落後人家二十年。英國在八十年代尾,已是一個講創意的國家,人家在教育上做了很多事情。
讀: 北歐的國家也是。
謝: 我不知道日本情況如何,就算其他亞洲國家,也不是很注重視覺的分析,但現在我們認識一樣東西是通過文字還是通過影像?大部分都是通過影像。其實攝影是影像最初階段的學習,你要學懂閱讀影像,要學懂怎樣欣賞一張相,這是基本的訓練。
中產社會的樽頸
讀: 就像我剛才說的十元鈔票事件,主流的中產社會對美學持一種很犬儒、很功能性的態度,談到設計就說見仁見智。
謝: 我最近去了幾次西九的討論,都是談很實際的問題,記得有個校長問,究竟由學校出發,我帶着百多名學生,車能不能抵達博物館門口?行五分鐘會有很多事情發生,不便老師管理。
讀: 整個社會都不追求美藝欣賞。
謝: 影像在這裏已經不是藝術,而是知識,是你去認識社會的基本知識,不要說藝術那麼高層次,事實上,現在你接觸的媒介大部分都是影像,你怎麼可以對你接觸最多的東西沒有認識、沒有研究?這是生存的基本知識,看一張相,你知道它在說甚麼嗎?
讀: 我是只重視相中的小籠包是否好吃,至於那張相片是杜可風的風格,還是謝至德的風格或Stanley Wong的風格,都不重要。大家只重視功能,就是小籠包是否拍得好吃。小籠包要拍得清,不要黑,一定要有煙,要色香味俱全。
謝: 正是因為這種基本要求,所以香港就那麼單一。每一張相都是一種價值取向,看一張相時,你已聯繫了這種價值取向。你看LV廣告和Giordano廣告,已經相連了,每張相都有一個價值。套用Foucault的理論,在圓形監獄的塔上面,只要有個守衞看下來,下面的人就會乖乖遵守,因為有權威存在。影像就是權威,你怎樣和周圍的人聯繫呢?就是他們今年穿甚麼我就穿甚麼,根本不會有獨立思考,不會有批判性思想,不會想想那是甚麼。香港是最極端的,滿街的廣告都比人還要大,像佛像,以前只會有佛像或教堂才會有這樣大的icon,現在佐敦道、彌敦道全部都是消費廣告,然後逼我和那些東西聯繫。教育制度只重視考試,如果大家中小學的訓練都是這樣,我想就算在大學接觸到其他東西,單一價值成形後,也需要很長時間去改變。
讀: 我覺得不只是攝影,主流社會的追求仍然停留在功能與實用層次,一張十元紙幣的設計是怎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不能被仿冒,就像對大館Herzorg本來的建築設計,大家只會想交通會不會超負荷?有沒有遮擋景觀?有沒有區內市民反對?沒有人去爭論美學層面,爭論在作品的設計中,體現了甚麼價值?
謝: 大部分我們在媒體中見到的和文化藝術有關的,都只是一些資料性的東西,並不是一些分析和評論的文章,只是幾時幾日有甚麼節目,那個節目有甚麼內容,那就完了,而不是批判的分析評論。我們連一份有分量的文化評論雜誌也生存不了。
讀: 所以我覺得那不只是影像教育的失敗,而是整個人文教育、通識教育的失敗。不只是對影像、視覺藝術的不重視,而是對所有和美學有關的東西都不重視。
謝: 再分得仔細一點,這城市就是太重視理性,欠缺了感性,我們的孩子也會去學芭蕾舞、鋼琴,但他們都是很理性的,要拿這些東西去過關,但有多少人考完八級鋼琴後,會在家裏彈奏,或者會買票去聽音樂會?香港投放在藝術培訓的資源是不少的,小朋友學跳舞、彈琴、打鼓、拉小提琴,很多很多,但小朋友有多enjoy?
讀: 因為學校不會教他們去感受和享受音樂,家庭就更加不會。
謝: 他們只知考到八級鋼琴就可以考到那間學校,並不會去欣賞音樂有多哀傷、多浪漫。
城市的歷史宿命
讀: 你認為這是殖民地的處境造成,因為殖民者不想你有獨立的文化身份、批判性思想,還是今日中國文化已經沒有人文精神的抒情感性,只剩下很功能性、很practical、很實用主義的思維?
謝: 你要比較一下大陸和台灣,台灣的情況比我們好很多。這究竟是殖民地遺留下來,還是這個社會實在太小,人口太少,因此所有東西都是基本要求,只是想到生存。但其實我們已經拋離了基本要求很久了。
讀: 所以我覺得這種「搵食格」是難民心態。因為我們是個移民城市,不是太遠,只是我們的上一代,由上一代帶下來給我們。上一代都叫我們不要學美藝、攝影,搵不到食,最好做工程師、律師、會計師。
謝: 我在Art School的經驗是這樣的,因為我們的programme是part-time的,大部分都是mature student,interview時,他們說的入讀原因大多相近,都是以前想讀,但父母不讓他們讀。我要做一份他們認可的工作,現在有錢了,我想做點自己喜歡的事情,這就是現實。他們或者是一名督察,又或者律師,這就是現實,更可悲就是他們讀完之後,都不會想以此為生。
我覺得是社會沒甚麼焦點,在八十年代時,覺得九七是個轉機,有個明確的方向,但九七後好像更沒有方向。
讀: 我讀大學的年代,八十年代中期,當時我覺得香港有一種很獨特的風格,即使去到台灣、東京或歐洲的城市,我作為香港人很容易在美學層面找到香港的風格。但九十年代到現在,尤其是九七後,你問香港風格是甚麼,其實是更加模糊。
謝: 在政府的層面更加是自亂陣腳、自廢武功。我經常問,我們的價值取向是不是真的要和大陸如此看齊呢?我們應該有足夠的空間去發展自己的東西,但這種東西沒有出現。
讀: 我覺得不是沒有出現,而是難產了。如果沒有九七問題,如果中產階級不是大量移民到北美洲,那種東西可以慢慢成長的。其實我們最終討論的是一種城市中產文化起落興衰。但這二十年,正正是香港人最折騰的時間,由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開始,基本法起草、前途談判、移民潮、回歸前政治鬥爭、回歸後是金融風暴。
謝: 無可否認,八、九十年代香港的廣告在世界上是行得很前的,但只限於廣告,你宣傳別人的東西做得很好,但你沒有自己的品牌。
讀: 很簡單,我看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很容易會看到維也納、布魯塞爾、巴黎和紐約現代主義藝術運動風格,體現在建築、文學創作、電影及影像創作中。當時的上海,是整個世界現代主義運動的一部分。
謝: 香港影像對大陸有個重要影響是改革開放後頭十幾年,當時攝影在大陸還不流行,香港的攝影師到大陸拍照,帶了一些新的東西進去,情況就如徐克、許鞍華在外國回來,把西方最前衞的東西帶到香港,香港又將這些東西帶到大陸。
但其實八十年代,香港的沙龍攝影對大陸的影響很大,只不過他們不能持續、不能過渡而已。因為我們現在不會再去追求那種詩情畫意。
十九世紀香港的巴斯商人。
吹出個未來
讀: 但是我們可否合力捧李志超做巨星呢?王家衛也是這樣做出來的。城市美學可否製造出來?變成一種香港美學理論。
謝: 但只有政府可以做到,而且香港對於美學方面,最缺乏的,正正就是理論。
讀: 香港是這樣醜的了,為甚麼那麼有錢的城市,卻沒有美麗的公共建築,因為我們的投標制度是價低者得,世界不會又價低又美的。但我們可否純粹Ad Hoc Based,影像也好、電影也好、建築也好,將香港的美學變成一種理論?
謝: 香港沒有。沒有人有這個能力。中大近幾年都在做香港的視覺年鑑,我記得幾年前已經出過一本由大陸的學者寫香港的美術史,問題是這個地方孕育不到人才。你看看大學裏的學者有多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想只有5%。大學裏有多少教授研究影像?在八間大學中,有幾多個教授是研究影像的?沒有。以前理工還有人寫過一些,但是現在已經不寫了,現在有理論出來嗎?
讀: 兩者是互相影響的。如果沒有杜可風、王家衛、徐克、杜琪峰,沒有香港電影,也不會有香港電影研究的學系。
謝: 但所謂東方荷里活也是先在荷里活研究然後再回來,是出口轉外銷,是人家講了東方荷里活,做了很多東西,然後香港才開始研究香港電影。你想想電影資料館成立了多久?大學資助的體制也是很實在的,要看有多少篇論文可以在外國刊登。你寫一篇研究香港影像理論的文章,可以在外國刊登嗎?如果體制是這樣,是很困難的。
讀: 說得俗一點,其實是要找班人「吹」得,如李歐梵寫《上海摩登》,只不過是將上海學理論化。香港的電影、攝影都可以「吹」出來。問題是有沒有人把這個東西變成brand。
謝: 我覺得這幾年攝影慢慢回來了,因為普及了,如今年第一次辦攝影節,爭取了資源,也吸引了更多媒體,也有很多學生來看,讓大家更容易關心。因為這兒真的是包羅萬有,但凝聚了氣氛,也有了資源之後,又要如何維持下去?在展覽之餘,亦要教育到一般人去認識如何欣賞影像。如果不是如此,又是那一句,完了之後就沒事。我覺得香港最大的問題是引發不起潮流。這是否和歷史有關?根本就累積不到,每一個年代都重新去講,從頭來過,還未完成、成熟的時候,那件事情就沒有了。然後大家又再來,再做過,永遠都上不去,永遠都是原地踏步,做到某個程度時,就會沒有了,要再來過。如果沒有那種歷史,不知道以前發生甚麼事,又怎可以上到去呢?特別是文化的事,這都不是突然間就飛下來、跌下來的,是有足夠的土壤來慢慢培養,才可以開花結果的,那才可以產生下一個世代。
香港這地方太現實,沒有人願意為這個地方犧牲去做一些事情。以我的講法來說,這是一個賭場,你入到賭場,賭完就走,你是不會去建設賭場的,你去賭之時,就已經建設了。
讀: 其實是我們香港人「吹大」了?覺得我們是world class,而我們根本不是紐約,我們頂多是芝加哥。
謝: 別想得美,我們連芝加哥也不如。在外觀上,香港可能是有機會,我們有IFC,海港兩邊每晚也有幻彩詠香江,但內裏甚麼都沒有。
讀: 索性我就當這兒是一個賭場,像是七人欖球賽,香港隊永遠是打最低級的銀碟賽,還並不一定勝出。較高級的銀盃和銀碗,都是斐濟、澳洲、紐西蘭這些強國奪得。但沒所謂,這也是香港的盛事,如果抱這種心態不就可以嗎?
謝: 但是你教育不到香港的人嘛!
讀: 做不到也沒辦法。
早夭的感性
讀: 我覺得香港奇就奇在,我不是說要為香港政府爭辯,而是政府每年給演藝的經費不少。學校、家長投放在學生身上的美藝教育,包括兒童繪畫班、音樂等也不少。其實說到底,我們老是從一個很功能主義的角度去面對美學這課題。這是一個思想上的問題,而不是經費足不足夠的問題。教育走向多元智能是正確,但是不能以這種功能主義的心態去做,因為從前就只要過一關小學會考,但現在就要過十關。因為每一個智能都是一關。這樣的話,那你的小孩想不死也很難。又或是在考完八級鋼琴,應付了父母的要求後,就不會再去彈鋼琴,也不會去聽演奏會,因為他們已變得很討厭音樂,我認識的很多人都是這樣。
謝: 問題是方法及重點放在哪裡。還有是很實際的看成績,比方說,鋼琴就是看你考到哪一級,而不是說享受。
讀: 就是沒有融入生活當中。比如說買畫或攝影作品,在外國買藝術品放在家中作室內擺設是很普遍的,是普通人都會做的事情,因為他們已經將之融入生活當中。但香港不是這樣的,你看在香港,那些所謂的豪宅,七百呎也沒有。
謝: 而且是賣過千萬的。
讀: 對。小孩子還要睡窗台,你還要我放幅畫在客廳?香港人就寧願買一幢會所有很大水晶吊燈的屋苑,有藝術品在會所展示更好,每一個來探我的人經過會所都會看到,這樣就夠了,我不用再在家裏擺放一幅攝影作品或者是畫。
謝: 這就是文化修養。為甚麼西方國家會覺得藝術教育這麼重要呢?
讀: 因為他們是真正的中產社會。
謝: 還有他們真的會用其他方法去調和生活,你看西方國家的人有空閒時間,香港人哪有時間去作文化消遣?我們九點上班,八點才下班。
讀: 當然啦,香港人很多都背負着幾百萬的按揭債務。
謝: 那就是了,那還可以說甚麼修養呢?八點鐘下班還怎會有閒情逸致去聽一場音樂會。
讀: 所以說,其實到了某一點就要放棄Art for Hong Kong這種想法。
謝: 我就不會說Art這個字,而是修養,你怎樣能將人的感性部分去掉。
讀: 但可以用消費主義來解決,例如劈綠茶溝威士忌加唱「夭心夭肺」的K歌,人的感性需求不就是成功解決了嗎?這才是香港之道。
謝: 如果是這樣就不要再說甚麼文化藝術,因為對於香港來說,是沒有意義的東西。但我就較為樂觀,影像的學習,懂得閱讀和解讀影像是一個基礎需要,而不是像懂得欣賞一幅水墨畫、油畫那樣富貴,而且人人也做得來。
讀: 那為何我不效法余若薇和湯家驊等政治明星,先做大狀賺個盆滿缽滿,人到五十才回過頭來為民主請命。為甚麼我廿幾歲就學做長毛、蔡耀昌那樣笨?你看主流傳媒是捧哪一些人?是「走精面」的,而不是堅持自己年青時代理想的。
謝: 所以也不會有藝術家出現,沒有堅持怎會有藝術家。
讀: 你相信誰堅持誰最終就會贏?
謝: 是的,藝術都是一樣。我們現在提及的大師有哪一個不是因為堅持。你不連續投身五、六十年,怎能成為大師呢?現在的人就抱着六合彩的心態,想一注獨中。現在是說藝術創作,我真的不相信有人能夠創作一樣藝術出來而能餬一輩子口。
讀: 藝術是不是對自己有一種內在的價值,能夠堅持下去?
謝: 所以回到藝術這個問題,最重要是intention怎樣。
讀: 我覺得最叻仔叻女,就是那些事業有成賺夠,到五十歲才找回自己理想的人,他們是sure win,既晋身主流精英,又「有型」而且受追捧,這是進化了的功能理性精英。
謝: 我說個例子給你聽。我有一個做大律師的學生,他來報讀攝影班,在過程中,他不斷投訴學校的機制,但我心想你學的是攝影,不能以其他的價值標準硬套下來,都不是這回事,可惜就是會有這些人出現。本來很高興他來尋回自己的理想,但另一方面同時會帶來其他的問題,影響了學習氣氛。所以那些事業有成的人,是否真心想學習,還只是為了填補心靈上的空隙呢?但我覺得這都是好事,起碼他有這樣的需求。但這又回到最低的標準了,香港永遠都是這樣,只會談有和無的問題,但不會去理會有和好的問題。
向最低看齊的社會
讀: 你不覺得香港現在愈來愈倒退?去到一個basic needs approach society,不犯法的事就可以做,榮譽已經不再重要。
謝: 就是沒有道德。
讀: 但你就一直要求我們積累,在說人文精神、城市美學、價值,而我們從七、八十年代一直倒退至只講rule of law的今天,整個城市愈來愈內向,只是希望不會被內地影響我們的法治。坦白說,香港的電影、香港的攝影、香港的文學創作,要怎樣呈現於中國及世界,一定要與香港整個社會位置有關。如果沒有了這樣東西,就算舉辦足十年攝影展,對香港,對我們要追求的,也是沒有幫助的。你看當所有東西繼續倒退,政府與商界會以為合法的事就可以做,賺錢的道德也不理會。
謝: 但你沒有核心價值就更糟了。
讀:但要做國際城市不可只得核心價值,然後甚麼也沒有的。如果只有rule of law就很簡單了。若我是藝發局,就只講公平、公開、透明,但這本來就是社會最基本的東西,現在就變成最高的操守要求,為甚麼會變成這樣的呢?我覺得這是因為回歸過後,我們仍沒有做到對自己身份的探索,為甚麼有這麼多人去做攝影創作,但仍然無人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謝: 其實也有,不過很少。
讀: 我覺得真是很少,如果你要留存後世或至少有價值,一定要令你的攝影作品不是存在於一個孤立的空間,縱向的要存在於香港歷史內,橫向的要存在於當下的社會環境。如果沒有了這個座標,就不用爭論了。
謝: 我只覺得在香港做任何的創作,都是很小眾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