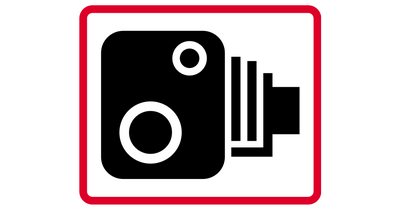旅遊攝影的道德

那天我躲在薩拉熱窩的咖啡店,一直埋首寫明信片給友人。潦草的字體寫滿了一張又一張,都在說所謂旅遊攝影的道德問題。友人們也許都覺我煩人,好端端的風光秀麗的明信片,背後卻是我零零碎碎的思考。
也許選擇走進波斯尼亞這片曾經的烽火大地,本就帶著某種我不願意承認的某種獵奇心態。薩拉熱窩城內,許多地區仍是一片頹坦敗瓦,一棟接一棟因政府資金短缺而無法清拆的危樓。水泥外牆密密麻麻的佈滿了彈孔,鋼筋爬出了瘡痍外殼。圍欄外有紅色大字警告行人:「ATTENTION! Dangerous Ruin」。
在這種時刻舉機難說不是自然反應,爾後卻不得不想--那種近乎興奮的心情是否全然出於好奇,還是對於我無從想像的,他人的恐懼與地球上另一端的苦難的無恥消費。讀過許多關於波斯尼亞那場曠日持久的戰爭的紀實小說,塞軍圍城時,許多薩拉熱窩人即使足不出戶也會成為流彈與迫擊砲的犧牲品,城內許多居民都死於盲飛的炮彈碎片而非有目標的子彈下。牆上的那些大小不一的坑洞,畢竟記錄過多少曾為生存苦苦掙扎而最終邃然消逝的生命。然而在我按下快門的那一剎那,卻驟覺我以為自己擁有的善良與惻隱到底有其制限,至少我無法想像那些與我從未活在同一時地的生命,在我記憶裡沒有臉孔與名字對應的人。此刻的我站在戰爭的遺跡下,卻與這地的歷史無從連結。我對於這些影像的興奮竟是難辨由來。

當然這究竟不過一種自以為是的,充滿知識分子潔癖的自省,到底不如戰地記者在藝術與人性之間的掙扎般涉及道德。最著名的例子自是南非戰地記者Kevin Carter 1994年在蘇丹拍攝的作品「飢餓的蘇丹」(The starving of Sudan)--瀕死的瘦弱女孩匍匐地上,身後是躍躍待餐的禿鷹。這幅蒼涼的影像最終為他贏得了普立茲獎,但也在掌聲中奪走了他的靈魂--Carter最終在自己的車子裡自殺身亡,在遺書裡說:「真的對不起,生活的痛苦遠遠超過了歡樂的程度。」
我至今無法想像Carter舉機一剎的心情與其後把他的靈魂消磨殆盡的夢魘。他與瀕死女孩的相遇究竟是個偶然,選擇美學與藝術興許亦是攝影記者本能。他近乎荒誕的死亡卻叫人不禁想像宿命,選擇與救贖的可能。
很自然地想到了Susan Sontag的「旁觀他人之痛苦」。我們對於沒有在眼前展現的戰爭與殺戮,電視畫面裡如電影特技般的炮火﹑坦克﹑難民與各種關乎死亡的血腥影像,有的不過是道德要求的,「負責任」的慈悲與同情心,廉價而淺薄。在戰火不會影響自身的前提下甚至會為某些影像感到興奮,如同Sontag所描繪的現代社會景象:過多的視覺刺激磨鈍了大眾的同理心和感官。當人看過一張又一張血腥照片後,裡頭的人和血肉即變得如此平面,最多叫人感到噁心,卻無法賦予同情。這也是攝影這項記錄當下的藝術的特殊性,美學與道德的交換。

“Sniper Avenue”
那個叫人沉溺的,孤獨的夏日,我躲在咖啡店裡寫下了凌亂的思緒,如熱鍋螞蟻。走到街上,在毒辣卻叫人倏然清醒的太陽下,我在人來人往的薩拉熱窩墟市找到這塊「Sniper Avenue」牌子。本能的皺眉:這樣的玩笑也能開嗎。腦子裡盡是童年時始反芻的戰爭浪漫符號,那雙在Sniper Alley(狙擊手之巷)殉情的小戀人,「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後來卻見許多餐館甚至紀念品都在販賣佔據九十年代國際新聞頭條的那場戰爭。消費戰爭浪漫的,又豈止生在和平時地的我。

舊城區一家波斯尼亞菜餐廳
——–
作者簡介
陳婉容
當上窮遊背包客多年,曾踏足近六十個國家。去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