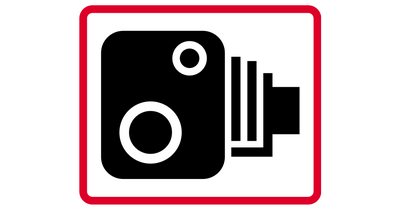〔特約轉載〕油麻地垃圾堆中的尼裔癮君子 一顆渴望被關懷的心

「好耐無見!做咩咁耐都唔嚟啊?」此等閒談,尋常不過,但對於Sing來說,已經是幾年來最真摯的問候。
因為他是早已被社會遺棄的無家者。
四十歲的Sing是尼泊爾矞港人,「家」住油麻地西九龍走廊橋底,大半年前,攝記在橋底垃圾堆中,一張破床墊上看見他,開始記錄他的生活,這是我們知道、卻不願意親眼目睹的香港。


Sing三年前落戶於此,拾荒維生。與大眾對無家者的印象有所不同,他非常注重個人衛生,每天用拾回來的洗頭水和沐浴露,到公園殘廁洗澡、洗衫,像要洗走毒癮,洗去以往每個錯誤的決定,找回那個純潔的自己。他更會花心思襯衫,在鏡前照了又照。有次攝記讚他:「你好大隻喎!」他卻黯然道:「我瞓街,無嘢食,成日肚餓,所以先咁瘦。」


三年來,每晚垃圾站工人收工他便開工,去拾舊電器,拆出銅線賣。他每天努力工作近十小時,變賣來的錢也不過值三元時薪,夠他買兩個麵包,吃一天。即使不夠吃,也只能捱著餓,明天重頭開始。
他把賺來的錢全部放在掛頸口袋裡,因為他連一個可固定儲存東西的地方也沒有,隨時會被偷。同時,政府為求驅逐無家者,手段層出不窮:把浴室上鎖、到處灑漂白粉、頻頻洗地、公園長椅加裝「扶手」、清晨出動保安驅趕,為要配合香港「乾淨城市」的形象,特別是西九這個豪宅集中地。


他祖父曾是英國陸軍啹喀兵,抗日戰爭時守衞香港邊防,是第一代居港尼泊爾人。Sing卻沒有因為他祖先的貢獻而得到任何優待,這些歷史就如政府期望香港的每條橋底和公園一樣,被清洗得一乾而淨。Sing的家每隔幾個月便會突然被清場,從沒被當成人看待。



Sing和很多第二、三代尼泊爾人一樣,沒有接受過中文或廣東話教育,語言障礙使他們難以融入社區,亦只能做低技術工作。Sing最初在餐廳工作,受朋友引誘,染上毒癮,五年前曾被迫戒毒,但不久又再次染上毒癮,「最危險係藥房買到嘅藥,例如咳藥水,我哋好容易會買嚟當毒品咁食。」
毒品令Sing脫離社會,社會也逐漸遺忘他。



因此,攝記的出現成為他唯一露出笑容的原因,漸漸地,他亦嘗試重拾人際關係。有次他拿起攝記的背包說:「你唔好孭咁重啦,好容易會受傷。」聖誕節前幾天,攝記如常來看他,和他聊天。正要轉身離開之際,Sing叫住了他:「我拾咗支筆,我又唔寫嘢,不如俾咗你。」攝記拒絕,他隨即補了一句:「當係聖誕禮物吧。」攝記心裏感動,自始隨身帶着。



有天攝記發現他皮膚嚴重潰爛並發燒,勸他去看醫生,他憤然道:「除咗你,無人真正關心我,嗰班道友唔係真朋友,只會叫我吸毒。」人非草木,無家者需要的跟普通人無異,同樣是一顆願意關懷的心。


兩者建立了關係,偏偏Sing卻有所顧忌。他讓攝記拍他洗澡,工作,睡覺,甚至吸毒,但唯獨一個地方他不願攝記跟來,總是推塘說:「呢啲地方好污糟,唔係你去嘅。」他不介意在攝記面前坦露自己的所有,卻不希望攝記忍受惡臭和踩入髒亂的垃圾站。


吸毒令他失去工作能力,最終露宿街頭。他深知毒品的禍害,每次「追龍」(吸食毒品)都會叫攝記不要靠太近,緊張地重複「千祈唔好吸毒,吸毒好恐怖,戒唔甩。」他很想念在尼泊爾的妻子和十二歲的女兒,但脫離不了毒品,亦只能記在心中。對上一次見面已是十年前,女兒牽着他牙牙學語,漸長成亭亭玉立的少女模樣,他都只能靠幻想。


幾個月前他被控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還押候審。攝記曾透過荔枝角收押所聯絡他,但沒有回音。Sing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橋底還有其他來自尼泊爾,巴基斯坦、印度和本地的無家者,而近年的無家者數目不斷上升。根據全港無家者人口統計行動,香港無家者(包括露宿、廿四小時快餐店無家者及臨時收容中心等)的數目由一三年的一千四百人增加至一五年的一千六百人,增幅為百分之十四,以九龍西的無家者數目最高。


















攝影:高仲明
撰文:關卓凌
圖文經由高仲明及壹週刊特許轉載